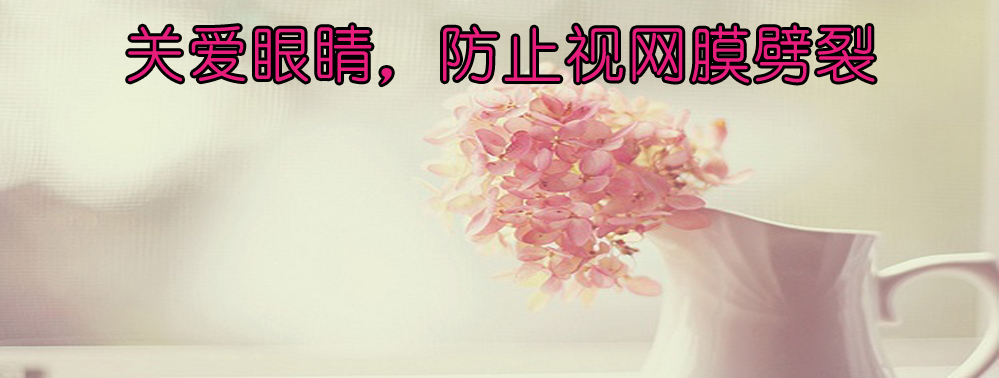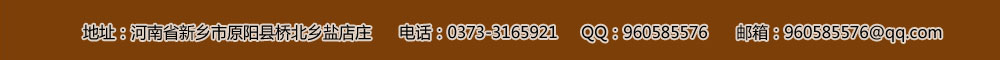基因治疗的前世今生番外新技术的伦理
回望过去二十年,伦理语境下的争论和批评似乎一直伴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年,在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降生的克隆羊“多利”引发了围绕克隆技术特别是克隆人的巨大争议,并促使各国政府迅速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条文;年在宗教保守团体的游说下,美国小布什总统签署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美国联邦经费用于发展新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系;年,哈佛大学因出现两只灵长类动物非正常死亡,彻底关闭了校内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而在美欧许多研究机构中对类人灵长类的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年春,伦理争议的焦点再次光顾生物医学领域,而这次在漩涡中心的是一种称为CRISPR的基因组编辑新技术。在三月初,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记者造访该技术应用的先驱之一,哈佛大学教授GeorgeChurch实验室,意外发现该实验室已经开始尝试在未成熟的人类卵细胞中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纠正BRCA1基因突变—该基因突变是女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罪魁祸首之一—从而为从遗传机理上预防相关癌症的发生提供临床上的可能性。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周之内久享盛名的《自然》和《科学》杂志纷纷发文,警告类似基因编辑操作存在未知的安全和伦理风险,呼吁停止利用类似技术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一个月后,来自中国中山大学黄军就实验室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ProteinCell)就将争议的水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在人类胚胎中进行了基于CRISPR技术的基因编辑操作。尽管黄声称实验所用的是本身存在缺陷、无法发育成成熟胚胎的受精卵,但是在很多批评者看来,类似操作已经与人工修改和制造人类本身无异。比Church实验室进行的生殖细胞修饰工作更进一步,黄所修改的受精卵已经携带了一个人类个体发育的全部遗传信息;如果植入女性子宫,就存在孕育出一个完整生命的可能。换句话说,至少从技术角度考虑,人类已经站在了人工修改和制造自身的门槛。在这里,笔者几乎不需要再次强调和引述基于伦理考量的批评。值得指出的是,批评者中也包括CRISPR的创造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Doudna教授。
然而在近乎一边倒的谴责和批评声中,笔者希望借此机会回顾历史,看看科学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漫长恩怨。
科学进步一直在推动和挑战伦理
由于生物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人类本身,与同样有什么药可以治白癜风青海治疗白癜风医院